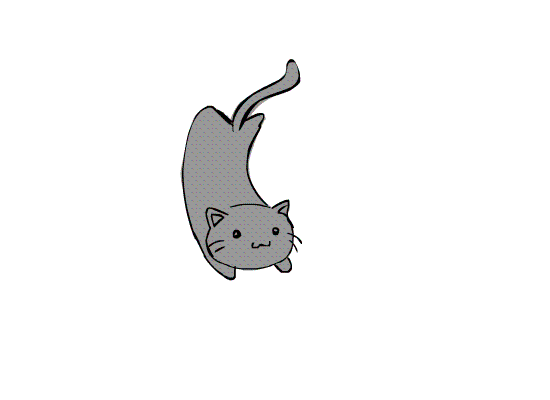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精神病院是否类似为了预防犯罪而提前将病人逮捕呢?即使是所谓自愿,但人怎会有放弃自由的自由。
人们怎能因为从未做过的事而付出代价呢?
对于有危害性的精神病人,或许只能在他们发病之后审判了吧?令人头疼的问题。
在父亲的葬礼上我一点也不因为他的死而感到些许沮丧与悲伤,唯一印象深刻的只剩葬礼那令人生理不适的气氛,管弦呕哑,哭啼遍野。
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的七年间,我只有寒暑假会与他们相见。其他时刻完全可以用渺无音训来形容。或许在某个时刻,他被我远远地抛到幼儿园地童年了,整个小学里,接近我的只有爷爷奶奶。
即使是在寒暑假,我也开始怀疑我对父母的笑是否是一种天衣无缝的伪装了,
真笑与假笑的区别或许就在于,是否可以随心而立刻停下。现在我对母亲的许多笑,显然是主动的,受控制的笑。
老莱娱亲似的。
存在回忆中的有几件事:低年级的我因为生气而回绝了跟母亲的许多次电话沟通,但随后收到母亲送来的塑料小兵人玩具时,愧疚与喜悦的并存似乎说明了我的生气同样是伪装的。伪装的情绪。
因为听班主任说,某同学家长在外工作,便驱车数百公里而来学校开短短的一次家长会…班主任莫名其妙的赞扬令当时的我厚颜无耻地对母亲提出了坐三小时车来开家长会的请求,后来母亲没来,也什么都没发生。
我只记得高速公路的两旁都是绿色掩映的山林,有如赛车游戏的地图那般。我坐在车上,有时一整趟都在看《爱情公寓》提前下载好的三集,有时也会睡觉。
初中
初中的体育课,当时我眼中如公生那样黑白的世界显然已不同于当时的同学。
“你看他如此忧郁”
阳光灿烂的水泥路上,赶赴宛如刑场的操场,同学不经意的评价不断回荡,回荡至现在。
面瘫哥
奇怪的称呼…奇怪的称呼…奇怪的称呼…奇怪的称呼…我好像从没向他人对自己的外号提过看法,即使之后的确有时不爽。
但也没到愤怒喊叫的程度。他们开心就可以了,我说真的。
同学失手扔向我的实心球没有使我躲开,当然他也没有扔中。我心中的确复杂的纠结了一瞬,但最终没有走开,看着红色的实心球从蓝色天空的背景中逐渐下降,逐渐向我靠近,两米远处的地面。大概是下意识的回避让我没被砸死。
“你的胆子真大呀~抱歉”
他绝对是我们这个年纪最纯真的人了,他有着大块头,但是却有着孩子的微笑,好像每个班都会有这样的人物。他挠了挠头,向我右侧走开,我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全是茫然与悲伤,茫然与悲伤的云一直笼罩至今。
为了迎合可能的习俗,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加平易近人,也许为了套取同学们的欢心或放心,在住校的第一天,在狭窄的寝室过道,我下铺的床上,我脱了个精光,战战兢兢带着洗发露和沐浴露去到沐浴房。纵使我在家一星期才被爷爷要求洗一次澡,洗一次头,在学校我却如此大胆。
呵呵
我想撕毁这段记忆。
ZYX
我小学的暗恋没有与我在同一个班级!!!!!呜呼!!!!!
我要死了,,,,,,
。。。。。。。。。。。。。。。。。。。。。。。。
我还是喜欢着她。她好可爱,上了高中之后,她好像还是如小学时那样可爱,那样可爱,
我很喜欢她的表情,那不是笑里藏刀的微笑,那是真诚的警敏,那是无法更加真实的表情,那是同我一样的,表情。
我仍然记得小学时她穿着毛茸茸可爱的衣服坐到我座位旁边,开始表演起英语单词。我清晰记得她衣服上有两个毛茸茸的小球,可爱极了。
她可爱极了。
我好想她。
但我根本没法跟任何人说话。
我根本没法跟任何人说话,因此我根本无法与她有任何交流,我似乎丧失了交谈的能力。
但是,,,,真的只要看见她,我就好开心啊。
2021年6月5日,在家悲伤地请假两星期,下周高考,被迫继续请假。
我每次都预定回学校就自杀。
但是,纵使在栏杆边想了一万次自己如体操运动院般攀上栏杆,身体探外,然后坠落在一滩血泊,
倘若一次都没有实践,怎能说他自杀的概率很高呢?
我们难道没有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杀吗?
16:57,头痛,晴,黄昏无